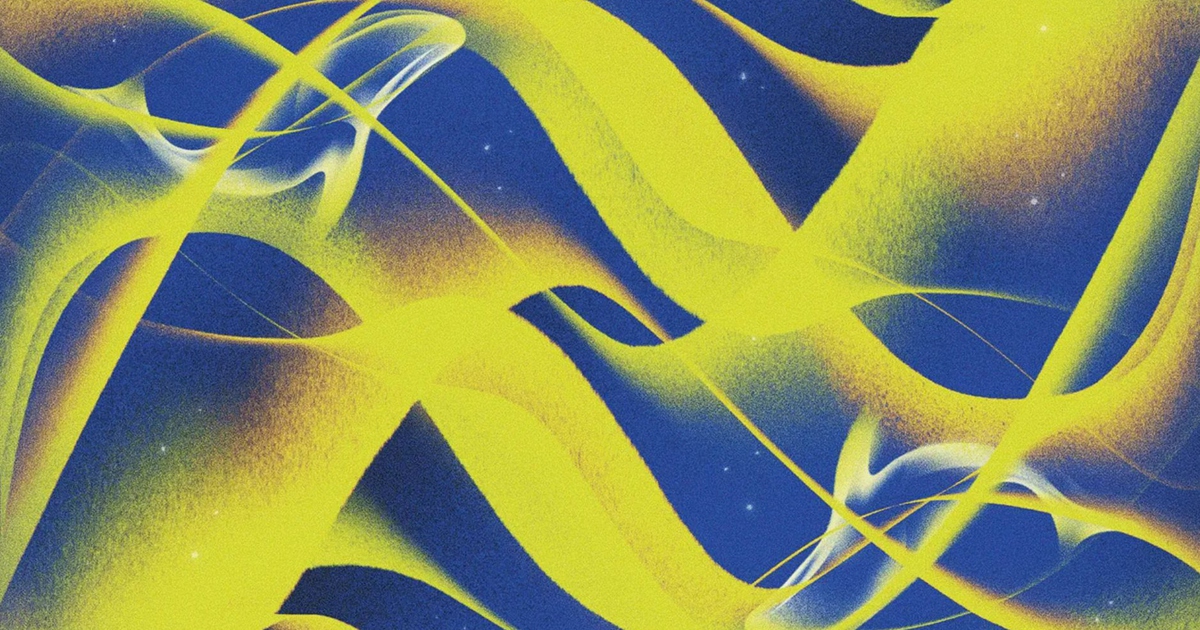
ADVERTISEMENT
一
蜜雪兒·芙奈特(Michelle Fournet)從未見過鯨魚,直到二十歲出頭。那時候,她一時興起,就搬到了阿拉斯加。她在一艘觀鯨船上謀到了一份工作。每一天,她都要在水面上,凝視著水面下移動的那些巨大身軀。然後她意識到,在她的一生當中,自然世界就在那裡,而她卻一直視而不見。 她回憶道:「我甚至都不知道我錯過了這些」。後來,作為一名海洋生物學研究生,芙奈特想知道她還錯過了什麼。她認識的一群座頭鯨她只能瞥見鯨魚身體的一部分。如果她能聽見它們在說什麼呢?她把一個水聽器扔進水裡,但傳過來的唯一聲音是船隻機械攪動的聲音。在機器的喧囂種,鯨魚們陷入了沉默。正如芙奈特發現了自然一樣,她也目睹了自然的退卻。她決定幫助鯨魚。為此,她需要學會如何去傾聽它們。
芙奈特現在是新罕布夏大學的教授,也是一個保護科學家團體的負責人,過去十年,她一直在對座頭鯨的聲音進行分門別類,記錄了它們平時發出的各種鳴叫聲、尖叫聲和歎息聲。鯨魚的語言龐大而多樣,無論是雄性還是雌性,不管是年輕還是年老,有一樣是它們都會說的。在我們聽力貧乏的人類的耳裡,聽起來就像是肚子裡咕嚕作響,間或還有水滴的聲音:嗚呼聲(whup)。
芙奈特認為,鯨魚透過嗚呼聲向彼此通報它們的存在。是表示「我在這裡」的一種說法。去年,作為驗證自己理論的一系列實驗的一部分,芙奈特駕駛一艘小船進入到阿拉斯加的佛雷德瑞克海峽,那是座頭鯨的食物,大批磷蝦出沒的地方。然後她播放了一系列鯨魚的叫聲並記錄下鯨魚的反應。回到海灘後,她戴上耳機,檢查重播的錄製音訊。先是響起了她播放出去的聲音。然後鯨魚的聲音從水中傳來:嗚嗚,嗚嗚,嗚嗚。 芙奈特是這麼描述的:鯨魚聽到了一個聲音在說:「我在,我在這裡,我是我。」他們回答說:「我也是,我在這裡,我是我。」
這種實驗叫做重播,生物學家用這種辦法來研究是什麼誘發動物說話。到目前為止,芙奈特的重播用的都是真實的鳴呼聲錄音。不過,這種方法並不完美,因為座頭鯨對自己交談的物件是非常在意的。如果鯨魚認出了錄音裡面的鯨魚聲音,會如何到影響它的反應?它對朋友說話和對陌生人說話有什麼不同嗎?作為一名生物學家,你怎麼確保發出的是中性的聲音?
答案之一是自己製作聲音。 芙奈特向地球物種專案(Earth Species Project)分享了她整理的座頭鯨叫聲目錄。這個專案由一群技術人員和工程師組成,他們的目標是在人工智慧的説明下開發出一種合成的叫聲。但他們打算模仿的不只是座頭鯨的聲音。這家非營利組織的使命是讓人類聆聽到整個動物王國的喧囂。他們說,30 年後,自然紀錄片將不需要像大衛·艾登堡(Attenborough)那麼舒緩的旁白,因為螢幕上動物的對話直接會有字幕呈現。就像今天的工程師不需要懂國語或土耳其語就可以用這些語言開發出聊天機器人一樣,很快就有可能開發出一個會說座頭鯨語、蜂鳥語、蝙蝠語或蜜蜂語的聊天機器人。
「解碼」動物間的溝通這個想法很大膽,也許甚至令人難以置信,但危機時期就需要大膽的、令人難以置信的舉措。凡是有人類存在的地方,動物都在消失。據一項估計,過去 50 年來,全球野生動物的數量平均減少了近 70%,而這還只是科學家實測到的危機的一部分。數以千計的物種可能會在人類對它們一無所知的情況下消失不見。
為了實現經濟脫碳,保護生態系統,我們當然不需要與動物交談。但我們對其他生物的生活瞭解得越多,我們就越能照顧這些生命。人類作為人類,會更加關注那些說我們的語言的人。 芙奈特表示,地球物種專案希望實現的那種互動能夠「幫助與自然脫節的社會重新與自然建立聯繫。」最好的技術為人類提供一種更充分地棲息在地球上的方式。從這個角度來看,與動物交談可能是其最自然的應用。
二
當然,人類一直都知道如何傾聽其他物種的聲音。歷史上漁民就與鯨魚和海豚合作過,為了的是互惠互利:一條魚留給它們,一條魚留給我們。在 19 世紀的澳大利亞,虎鯨群會將須鯨趕到捕鯨者定居點附近的海灣,然後用尾巴拍水提醒人類準備好魚叉。 (作為交換,幫忙的虎鯨可以先分到它們最喜歡的部分,也就是嘴唇和舌頭。) 與此同時,在白令海峽冰冷的海水中,因紐特人在狩獵前會傾聽弓頭鯨的聲音並與之交談。正如環境歷史學家芭絲謝芭‧德穆斯 (Bathsheba Demuth) 在《浮動的海岸》(Floating Coast)這本書裡所寫那樣,因紐特人把鯨魚看作是「擁有自己國家」的鄰居,它們有時候會選擇將自己的生命獻給人類——如果人類值得自己犧牲的話。
商業捕鯨者的做法就不一樣了。他們把鯨魚看作是浮動的鯨脂和鯨須的容器。 19世紀中葉的美國捕鯨業,以及下一個世紀的全球捕鯨業,幾乎消滅了好幾個物種,是人類造成的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野生動物死亡事件之一。 這種行為在20世紀60年代達到了巔峰,供有70萬頭的鯨魚被捕殺。然後,發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我們聽到鯨魚在唱歌。在前往百慕大的途中,生物學家羅傑‧佩恩(Roger Payne)與凱蒂·佩恩(Katy Payne)夫婦遇到了一位美國海軍工程師,法蘭克·瓦特靈頓(Frank Watlington),他為夫婦倆提供了一段他在海底深處捕捉到的錄音,那段聲音的旋律很奇怪。幾個世紀以來,水手們一直在講述著從木制船殼發出的怪異歌聲的故事,有人說這聲音來自他們不認識的怪物,有人說是來自海妖。瓦特靈頓則認為這些聲音來自座頭鯨。去拯救它們吧,他告訴佩恩夫婦。兩人確實開始行動了,夫婦倆後來發行了一張專輯,名字叫做《座頭鯨之歌》,進而讓這些會唱歌的鯨魚名聲大噪。一場拯救鯨魚的運動很快開始。 1972年,美國通過了《海洋哺乳動物保護法》; 1986年,國際捕鯨委員會取締了商業捕鯨行為。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裡,鯨魚在公眾眼裡已經變成了溫柔有智慧的海洋巨人。
今年年初已去世的羅傑‧佩恩常常會談起自己的一個信念,那就是公眾對鯨魚「稀奇而迷人的事情」瞭解得越多,關心它們命運的人就會越多。在他看來,光靠科學永遠無法改變世界,因為人類不會對資料做出反應,人類只會對情緒做出反應——對那些讓他們深受觸動而落淚或興奮到發抖的事情做出反應。他支持搞野生動物旅遊、動物園,認可圈養海豚做表演。他認為,不管這些會對動物個體造成怎樣的傷害,相比之下物種的滅絕也要嚴重得多。從此以後,環保主義者一直堅信與動物接觸可以拯救它們。
基於這個前提,地球物種組織來了一次富有想像力的飛躍,他們認為人工智慧可以幫助我們與動物進行首次接觸。這家組織的創始人艾薩·拉斯金(Aza Raskin)和布里特·塞爾維特萊(Britt Selvitelle)都是數位時代的建築師。拉斯金是在矽谷長大的;他的父親在 20 世紀 70 年代啟動了蘋果的 Macintosh 項目。在職業生涯的早期,拉斯金幫助開發出Firefox,並在 2006 年發明了無限滾動(編者注:infinite scroll,一種UX設計,可以讓使用者連續不斷地滾動查看更多內容,而不需要點擊翻頁按鈕),這既可以說是他最偉大也可以說是最不光彩的遺產。一番悔悟之後,他曾計算過自己的發明浪費了多少人類時間,得出的數字是每週浪費了超過了100000 條人命。
拉斯金有時會去一家叫做 Twitter 的初創公司閒逛,在那裡他結識了Twitter 的創世員工塞爾維特萊。兩人開始保持聯繫。 2013年,拉斯金在廣播聽到了一則新聞報導,內容是說衣索比亞狒狒交流節奏與人類語言是很相似的。事實上,相似到首席科學家有時候聽到背後一個聲音在跟他說話,然後一轉身才驚訝地發現那是一隻狒狒。採訪者詢問有沒有辦法知道狒狒在說什麼。對方回到沒有辦法,但拉斯金卻在想,有沒有可能透過機器學習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他向對動物福祉感興趣的塞爾維特萊提出了這個想法。
有那麼一段時間一來,這個想法就只是想法而異。但到了在 2017 年,新的研究表明,機器可以對兩種語言進行翻譯,而且不需要接受雙語文本的訓練。谷歌翻譯一直在模仿人類使用字典的方式,只不過速度更快、規模更大。但這些新的機器學習方法完全繞開了語義。它們將語言看作是幾何形狀,然後從中找出形狀重合之處。拉斯金在想,如果一台機器可以在不需要事先理解的情況下將任何語言翻譯成英語的話,那麼它時不時也可以對狒狒的喔喔聲、大象的次聲以及蜜蜂的搖擺舞做同樣的事情?一年後,拉斯金與塞爾維特萊成立了地球物種這個組織。
拉斯金認為,竊聽動物的能力將會引發一場歷史意義堪比哥白尼革命一樣的典範轉移。他喜歡說「人工智慧就是現代光學的發明」。他的意思是,就像望遠鏡的改進讓 17 世紀的天文學家能夠意識到新發現的恒星並最終摒棄了地心說一樣,人工智慧也將幫助科學家聽到靠靠耳朵無法聽到的聲音:動物說話是有含義的,並且其方式超乎了我們的想像。它們的能力,他們的生命,並不比我們遜色。 拉斯金說:「這一次,我們將放眼宇宙,發現人類並不是中心」。
剛開始那幾年,拉斯金與塞爾維特萊會跟生物學家會面,然後跟著他們進行實地考察。他們很快意識到,擺在他們面前最明顯、最緊迫的需求並不是煽動革命。而是對資料進行排序。二十年前,一位靈長類研究人員會站在樹下,將麥克風舉在空中,直到她的手臂感到疲倦為止。現在,研究人員可以將可擕式生物記錄器固定在樹上,並採集一年時間的連續音訊流。由此產生的數TB資料已經是任何一支研究所學生團隊都很難處理的。但是,將所有這些材料輸入給經過訓練的機器學習演算法之後,電腦就可以掃描資料並標記出動物的叫聲。它可以區分鳴呼聲與囀鳴聲的不同。它可以區分一隻長臂猿的聲音與她哥哥聲音的不同。至少,希望能做到這樣。這些工具需要更多的資料、研究和資金。 地球物種組織有 15 名員工,有數百萬美元的預算。他們與數十名生物學家合作,開始在這些實際任務上取得進展。
他們的一個早期專案面臨著動物交流研究當中最重大的挑戰之一,即也就是雞尾酒會問題:當一群動物在互相交談時,你怎麼知道誰在說什麼?在公海裡,成群的海豚會同時發出上千種強烈的吱吱啾啾聲;記錄這些聲音的科學家最終得到的音訊混雜著吱啾聲和哢嗒聲,就像體育場裡大家歡呼雀躍的聲音一樣。寬吻海豚聲音專家萊拉‧賽伊(Laela Sayigh)表示,即便是只有兩到三隻動物的音訊也常常沒法使用,因為你沒法分辨一隻海豚在什麼地方停止說話,另一隻海豚在什麼地方開始說話。 (就算錄製影片也沒什麼説明,因為海豚說話的時候不會張嘴。)地球物種利用了賽伊整理的大量海豚音特徵資料庫,開發出一個神經網路模型,進而區分出重疊在一起的動物聲音。這個模型僅在實驗室條件下有用,但研究就是要建立在它的基礎之上的。幾個月後,Google人工智慧發表了一個用於解析野鳥鳴叫的模型。
海豚大規模擱淺的情況在全球某些地方屢見不鮮。賽伊提出,有一種工具可以充當這種情況的緊急警報。她住在麻塞諸塞州的科德角,這裡就是發生這種情況的熱點地區,每年都會有十幾次海豚群體迷失方向,無意間遊到岸上擱淺導致死亡的情況。賽伊說,幸運的是,可能有一種辦法可以在這種情況發生之前做出預測。她推測,當海豚感受到壓力時,它們發出的標誌性吱啾聲的頻率會比平時高,就像暴風雪中迷路的人可能會驚慌地大喊大叫一樣。經過訓練來監聽這些海豚音的電腦可以發送警報,提示救援人員在海豚擱淺之前改變它們的路線。 2018 年,在薩利希海這個地方,一頭母虎鯨拖著餓死的小虎鯨的屍體在遊走,這一幕讓全球唏噓不已。為什麼人們會發現虎鯨?因為這裡有一個由 Google AI 建立的警報系統,可以監聽當地虎鯨的活動,並讓船隻避開它們。
對於研究人員與自然資源保護主義者來說,機器學習的潛在應用幾乎是無限的。地球物種並不是唯一一家致力於破譯動物交流的組織。CETI就是其中之一,這個非營利組織今年在多明尼加建立了一個研究抹香鯨之間如何交流的基地。在自己人生的最後幾個月裡,佩恩曾為 CETI 提供過建議。在今年六月的《時代》雜誌上,他寫道: 「不妨想像一下,如果我們瞭解動物之間的對話的話會怎樣;如果我們知道它們的腦子裡在想什麼,它們喜歡什麼、害怕什麼、渴望什麼、回避什麼、討厭什麼、對什麼感興趣、什麼是它們珍視的東西?如果我們知道這些會怎樣?」
地球物種這個組織迄今為止開發的許多工具提供的更多的是基礎工作,而不是直接的實用工具。儘管如此,這個新興領域仍充滿樂觀情緒。幾位生物學家告訴我,只要有足夠的資源,解碼動物語言是可以用科學的方式實現的。這只是開始。真正的希望在於彌合動物體驗與我們體驗之間理解上的鴻溝,不管這道鴻溝是多麼巨大或多麼狹窄都要彌合它。
三
艾瑞·佛瑞德蘭德(Ari Friedlaender)手頭就有地球物種想要的東西:大量的資料。佛瑞德蘭德在加州大學聖克魯斯分校研究鯨魚的行為。他一開始的工作是打標籤:當船隻在追逐鯨魚時,他會站在船沿努力保持平衡,然後舉起一根末端附有生物記錄標籤吸盤的長杆,當鯨魚付出水面時將標籤拍在鯨魚的背上。這件事情比聽起來要難。佛瑞德蘭德證明自己擅長這個——「我在大學就玩體育,」他解釋道——並且很快就開始了在海上打標籤的探險活動。
佛瑞德蘭德使用的標籤捕捉到大量資料。每個標籤不僅記錄了鯨魚的 GPS 位置、溫度、壓力和聲音,還記錄下高解析度影片與三軸加速計數據,後者與 Fitbit 用來計算步數或測量深度睡眠的技術相同。總而言之,這些資料以電影般的細節展示了鯨魚一天的生活:它的每一次呼吸,每一次潛水,它穿越了遍佈海蕁麻和水母的區域,它與撚轉的海獅相遇。
佛瑞德蘭德向我展示了他根據一個標籤的資料製作的動畫。在動畫中,鯨魚緩緩而下並在水中盤旋,遊走在彩色的三維路線上,就像穿行於海底瑪莉歐卡丁車賽道一樣。另一各動畫展現了幾頭鯨魚在吹出一張泡泡組成的網,這是一種捕食策略,就是機頭鯨魚圍繞在魚群周圍轉圈,用氣泡牆將魚困在中間,然後再張開嘴猛衝進去。在觀察鯨魚的行動時,我注意到雖然大多數鯨魚都沿著整齊的螺旋線遊動,但其中有一隻鯨魚卻走出了笨拙的「之」字形。佛瑞德蘭德說: 「那可能是只菜鳥。它還沒弄清楚技巧。」
佛瑞德蘭德多方面的資料對於地球物種他們來說特別有用,因為就像任何生物學家都會告訴你的那樣,動物的交流並不純粹靠口頭,它們對手勢和動作的運用頻率就像發聲一樣頻繁。多樣化的資料集讓地球物種舉例開發出適用整個動物界的演算法更接近了。該組織最近的工作重點是基礎模型,也就是為 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慧提供支援的那種計算。今年早些時候,地球物種發表了第一個動物交流基礎模型。目前這個模型已經可以準確地對白鯨的叫聲進行分類,地球物種計畫將這個模型應用到不同的物種身上,比方說猩猩(發出吼叫聲)、大象(透過地面發出地震般的轟鳴聲)以及跳蛛(通過振動腿部發聲)。 地球物種首席執行長凱蒂·薩卡里安(Katie Zacarian)是這麼描述這個模型的:「一切都是釘子,而它是把錘子。」
地球物種人工智慧的另一個應用是生成動物的叫聲,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GPT 的音訊版。拉斯金製作了幾秒鐘的禿鷹鳴叫聲。如果你感覺這一步似乎領先於對動物聲音的解碼的話,事實證明,人工智慧更擅長說話而不是理解。地球物種發現,它正在開發的工具很可能可以在實現對動物的聲音進行解碼之前先做到跟它們交談。比方說,很快就有可能用鳴呼聲來提示人工智慧,並讓它繼續用座頭鯨語進行對話——在人類觀察者不知道機器或鯨魚在說什麼的情況下。
沒有人預料到會出現這樣的場景。一方面,這在科學上是不負責任的。跟地球物種合作的生物學家做這件事情是受到知識的驅使而為,不是為了對話而對話。地球物種高級人工智慧研究顧問費利克斯·艾芬伯格(Felix Effenberger)告訴我:「我不認為我們會有英語-海豚語翻譯員這樣的人,好嗎?你把英語輸入到智慧型手機,然後它就會發出海豚的聲音,然後海豚就會飛奔給你取回一些海膽。我們的目標是先要發現基本的溝通模式。」
那麼與動物交談看起來、聽起來會是什麼樣的呢?未必得是形式自由的對話才能令人驚訝。就像 芙奈特播放的那些聲音那樣,以受控的方式與動物交談對於科學家理解它們的嘗試來說可能至關重要。畢竟,你不會靠在柏林參加聚會然後默默地坐在角落裡來學習德語吧。
鳥類愛好者已經在利用app從天上捕捉旋律並辨識是哪個物種在唱歌。有了人工智慧充當你的動物翻譯官之後,想像一下你還能學到什麼。你提示它製作兩隻座頭鯨相遇時發出的聲音,它就會發出一聲鳴呼聲。你提示它發出小牛對媽媽說話的聲音,它就會發出一陣耳語。你提示它發出失戀男性的聲音,它就會製作出一首歌。
四
人類倒是沒有趕盡殺絕過任何一種鯨魚。但這很難說成是一場勝利。數位只是生物多樣性的衡量標準之一。動物生活的豐富多彩在於它們的所說所為,在於它們的文化。雖然座頭鯨的數量自半個世紀前的最低點以來已經有所反彈,但與此同時,它們又失去了哪些歌、哪些習俗?被捕殺到僅占種群數量百分之一的藍鯨,可能已經幾乎失去了一切。
聖安德魯斯大學生物學家克里斯蒂安·魯茲(Christian Rutz)認為,(動物)保護的基本任務之一是保護非人類的生存方式。他說: 「你不會問它們,『你在不在?』你要問的是,『你在那裡快不快樂?』」
魯茲的研究物件是夏威夷烏鴉。他想瞭解自 2002 年夏威夷烏鴉在野外滅絕以來,其交流方式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這些引人注目的鳥類(已知會使用工具的少數物種之一)大約還剩下 100 只被圈養著,自然資源保護主義者希望最終將它們重新放歸野外。但這些烏鴉可能還沒有做好準備。有證據表明,被圈養的鳥類已經忘了一些有用的詞彙,比如保衛領地以及警告掠食者的叫聲。魯茲正在與地球物種合作開發一種演算法,希望能篩選出已滅絕的野生烏鴉的歷史記錄,提取出所有烏鴉的叫聲,並給它們貼上標籤。如果他們發現某些叫聲確實失傳了,自然資源保護者可能會生成這些叫聲,教被圈養的鳥類學會。
魯茲的態度很謹慎。他表示,生成叫聲必須是經過深思熟慮後做出的決定,必須在時間需要的時候才做。在今年 7 月《科學》雜誌發表的一篇論文中,他讚揚了機器學習的非凡用途。但他警告說,人類在干預動物生活之前應該認真思考。正如人工智慧的潛力仍然未知一樣,這也可能回帶來超出我們想像的風險。Rutz以座頭鯨為例。這些動物每年都會創作新歌,這些歌曲會像熱門單曲一樣傳播到世界各地。如果這些鯨魚熟悉了人工智慧生成的習語,並將其融入到它們的日常生活當中的話,人類就將改變其已有百萬年歷史的文化。 他告訴我:「我認為這屬於應該被限制使用的系統之一,至少目前如此。誰有跟座頭鯨聊天的權利?」
不難想像與動物對話的人工智慧可能會被濫用。二十世紀的捕鯨者就採用了當時的新技術,他們發射出特定頻率的聲納,讓鯨魚驚慌地浮出水面。但人工智慧工具的好壞取決於人類用它們來做什麼。湯姆·穆斯蒂爾(Tom Mustill)是一位保護紀錄片製作人,也是《如何說鯨語》(How to Speak Whale)一書的作者。他建議加大為動物解碼研究提供資源的力度,提供的資源要像最受擁護的科學事業,如大型強子對撞機、人類基因組計畫以及詹姆斯‧韋伯太空望遠鏡獲得的資源一樣多。他告訴我: 「現在的技術那麼多,卻只能留給開發出這些技術的人隨心所欲,直到世界其他地方的人趕上為止。不能讓這種事情發生,這一點太重要了。 」
數十億美元的資金正在流入人工智慧公司,其中大部分是為了企業利潤:更快地編寫出電子郵件、更有效地創作出存貨照片、更高效地投放廣告。與此同時,自然世界還是一樣的神秘。科學家們確切知道的為數不多的事情之一,就是他們知道自己有很多事情不知道。當我問佛瑞德蘭德,花了這麼多時間追逐鯨魚是不是讓他學到了很多關於鯨魚的知識時,他告訴我,他有時候會給自己做一個簡單的測試:鯨魚潛下水裡之後,他會試著預測鯨魚接下來會出現在哪裡。 他說:「我閉上眼睛說,‘好吧,我這輩子給鯨魚貼了1000 個標籤,我已經看過所有這些資料。我感覺鯨魚就要到這裡來了。’ 確實,鯨魚總是出現在那兒。但我不知道這些動物在做什麼。」
五
如果你能和鯨魚說話的話,你會說什麼?你會去問White Gladis 嗎?今年夏天,這只虎鯨因在伊比利亞海岸附近弄沉了一條遊艇而成為模因,你會問她是什麼激發了她的暴行嗎——是出於樂趣、妄想還是復仇?你會告訴Tahlequah,那位因為孩子夭折而悲痛的虎鯨媽媽,你也失去了一個孩子嗎?佩恩曾經說過,如果有機會跟鯨魚交談的話,他希望聽到它日常的那些八卦:愛情、世仇、不忠。另外:「說聲對不起也是很好的。」
還有那個古老而棘手的哲學問題。關於環境的問題,以及作為一隻蝙蝠、一頭鯨魚或你自己是什麼感覺。就算我們可以與鯨魚交流了,我們能理解它在說什麼嗎?或者它對這個世界的感覺,它的整個意識秩序,會變得太過陌生以至於難以理解嗎?如果機器把人類語言以重疊的形狀來呈現的話,那麼英語可能是一個甜甜圈,而鯨魚的就是一個洞。
也許,在你能夠與鯨魚交談之前,你必須知道擁有鯨魚的身體是什麼樣的感覺。那是一個比我們的身體還要古老5000萬年的身軀。它們的體型適合大海,可以毫不費力地穿越深淵,靠絕對的品質來對抗寒冷。作為鯨魚,你可以選擇什麼時候呼吸或不呼吸。大多數時候你都會屏住呼吸。因此,你沒法聞到或嘗到東西。你沒有手,沒法伸出去觸摸東西。你的眼睛還能正常工作,但陽光很難穿透水。通常在霧天裡甚至沒法辨認出自己的尾巴。
如果沒有你的耳朵的話,你就會生活在一片令人絕望的空寂之中。相對於在空氣裡,聲音在水裡的傳播距離更遠、速度更快,你的世界因此被它照亮。對你來說,海洋的每一個黑暗角落都可以充滿聲音。你可以聽見雨打在地表時淅淅瀝瀝的聲音、磷蝦遊走時的嗖嗖聲、石油鑽探時的爆炸聲。如果你是抹香鯨,你的半輩子都會在漆黑的深海中度過,只靠耳朵來捕獵烏賊。就像人類一樣,你也用聲音說話。但你的聲音並不像在稀薄的空氣中那樣會立即消散,而是可以持續存在。有些鯨魚的叫聲比噴氣發動機的聲音還要大,它們的叫聲能跨越海底,傳到一萬英里之遙。
但作為一條鯨魚,你的感覺如何?你有什麼想法,有什麼感受?對於科學家來說,這些是更難瞭解的事情。觀察你如何與同類交談可以得到一些線索。如果你出生在虎鯨群體裡,關係機密且排外的話,那麼你奶奶和你媽教給你的第一件事就是你的氏族名稱。歸屬感必須是必不可少的。 (還記得電影《人魚童話》(Free Willy)裡面的虎鯨 Keiko 嗎?等到它老了之後被釋放回家鄉水域時,它已經沒法重新加入野生鯨魚的家庭,而是只能再回到人類那裡,孤獨死去。)如果你是雌性抹香鯨,你會透過哢嗒聲聯絡部落成員,讓它們協調誰來照顧誰的孩子;與此同時,抹香鯨幼兒也會用咿呀聲回答。你一直都在忙個不停,不斷游向新的水域,進而養成一種時刻緊張警惕的性格。如果你是一頭雄性座頭鯨,你會把時間花在冰冷的極地水域,獨自唱歌,遠離你最近的同伴。不過,人類據此推斷座頭鯨很孤獨是錯誤的。對於聲音能傳到大洋彼岸的鯨魚來說,也許距離並不意味著孤獨。也許,當你唱歌的時候,其實就是在互相交流。
六
蜜雪兒·芙奈特在想:我們怎麼知道鯨魚會想跟我們對話呢?對於座頭鯨,她最喜歡的一點是它們的冷漠。她告訴我: 「這種動物有 12公尺多長,重達 34 噸,它根本不在乎你。它的每一次呼吸,都要比我的整個存在偉大得多。」羅傑‧佩恩也觀察到了類似的情況。他認為,對於一項原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來說,鯨魚是唯一能夠勝任這項任務的動物。什麼任務?讓人類感到自己的渺小。
這裡是加利福尼亞州,蒙特雷。一天清晨,我登上了一艘觀鯨船。那裡的水是石板灰色的,波峰則泛著白色。海面上有成群的海鳥掠過。然後三隻座頭鯨出現了,它們的背部整齊地露出水面。它們的尾巴偶爾也會閃現,這對拍攝這群座頭鯨的攝影師來說是有好處的。鯨魚崎嶇的脊線就像指紋一樣,可以用來區分鯨魚個體。
後來,我將其中一隻鯨魚的照片上傳到Happywhale上面。這個網站使用了一個針對鯨魚尾巴做出修改的臉部辨識演算法來辨識鯨魚。我送交的那頭座頭鯨尾巴上長滿了藤壺,對方給我返回了一頭標識碼為 CRC-19494 的鯨魚。十七年前,人們在墨西哥西海岸發現了這頭鯨魚。從那時起,它就一直在巴哈與蒙特利灣之間的太平洋上來回游走。有那麼一刻,我對這個網站能夠如此輕鬆地從大海中找出一頭動物並返回一個名字給我感到印象深刻。但話又說回來,我對這條鯨魚瞭解多少?它是母親還是父親? Happywhale上的這條鯨魚真的快樂嗎?人工智慧並沒有給出答案。我搜尋了這頭鯨魚的個人資料,上面只有一系列從不同角度拍攝的,纏滿藤壺的鯨魚尾巴照片。目前為止,我知道的就只有這些。
請注意!留言要自負法律責任,相關案例層出不窮,請慎重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