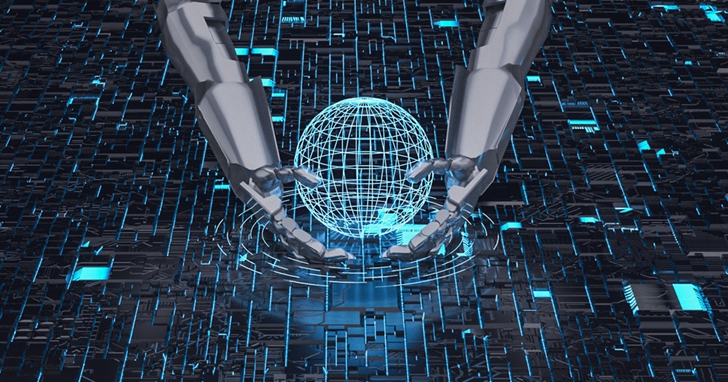
新的十年開始了,但這似乎不是我們想要的未來。可是,你知道40年前的科幻小說是怎麼預測2020年代的嗎?看看《銀翼殺手》、電馭叛客以及奧克塔維婭·巴特勒(Octavia Butler)筆下的我們正在進入的2020年代,你會對那種預測的準確性感到害怕。Tim Maughan為我們回顧了若干描寫到2020年代的科幻小說,但就像他最後總結那樣,科幻小說從來都無關未來,而關乎的是現在。寫未來顯然會折射講述的那個時期的願望、關切和恐懼。
👉 歡迎加入T客邦telegram ( https://t.me/TechbangNEWS )
當你在想像未來的時候,你想到的第一個時間點是什麼?2050年?2070年?那應該是在你有生之年的範圍,但又足夠遙遠,遙遠到有點神秘,不在我們掌握範圍之內的時間點。對於我們這些70年代、80年代以及在那幾十年工作的許多科幻小說家來說,2020年代感覺就像那樣的未來。這是我們大概能活著看到,但距離我們似乎還很遙遠的的十年,它可能是一個充滿了新技術、社會運動或政治變革的世界。一個敵托邦,也可能是烏托邦;一個既陌生又熟悉的世界。
當然,那個未來就是現在。去年是雷利·史考特(Ridley Scott)的科幻電影傑作《銀翼殺手》(Blade Runner,1982)的背景從未來滑向過去的標誌性時刻——這部電影的設定就是2019年11月——催生了數十部與之相似的熱門作品。不過,說到描寫不久的將來的2020年代的科幻電影和小說時,《銀翼殺手》的確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看著我們是如何悶悶不樂地步入到2020年代,現在我們有機會用事後諸葛亮的視角來評估一下那些作品。哪些是預測對了的?哪些令當年的想像看起來過時了?為什麼?而我們又能從過去的作家和猜測者對未來的預測當中學到什麼呢?
就像1980年代及之後的許多對未來的設想一樣,這個故事始於電馭叛客(Cyberpunk)。早在1980年代,在電影和視訊遊戲讓電馭叛客淪為大量缺乏想像的暴力和身體改造的比喻之前,這種體裁還是一種文學運動,正忙著把我們對甚囂塵上的資本主義,過度飽和的媒體,以及新興的電腦網路的擔憂推向虛構的未來。「電馭空間」(cyberspace)這個詞是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神經喚術士》(Neuromancer ,1984)及其相關的短篇小說創造和普及的。但鮮為人知的是,這位作家對高度聯網的世界的探索也同樣具有影響力。這部小說同時也是對那個世界的首次詳細探索。
《網路島》(Islands in the Net)
布魯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

Bruce Sterling的《網路島》(1988)的時間設定是2023年,這部書描繪了一個被類似網際網路(簡稱為Net)的東西所消耗的世界。Net容納著龐大的去中心化的跨國公司,也受其所控制。雖然網路島因預見了所謂的免費網路會變得如何的壟斷而聞名,但其最令人不寒而慄的預測是,在國營企業與反對自上而下的全球化的恐怖主義數據海盜之間,用無人機進行的一場永不休止的戰爭:
當他們定位到那些盜賊時,便用無人駕駛飛機去攻擊他們……他們是專家,技術人員。他們在黎巴嫩、阿富汗、納米比亞學到了東西。怎麼去打第三世界的人又不讓他們碰到你。他們甚至不看對方,就算看也是通過電腦螢幕…… 小巧,安靜,遠端控制。在沒人看的地方打仗。
Sterling對戰爭的預測令人著迷之處是,乍看之下,他似乎沒有理會戰爭本身的原因是什麼。《網路島》要說的不是不是我們經常被告知正在打的西方政府與伊斯蘭恐怖主義永無休止的衝突,而是發展中國家與全球化本身之間的戰爭。1980年代的經濟繁榮見證了全球市場的開放,跨國公司的實力大為增強,甚至對政府和民族國家的作用都構成了威脅。這些公司不斷用同質性不可阻擋的自由市場經濟,千篇一律的消費品牌,以及熟悉企業標誌來碾壓他們。
《網路島》的世界裡面到處都是看起來跟記錄表現數據的Apple Watche和Nike跑鞋非常相似的消費類設備。
當然,你只需看看真正的所謂反恐戰爭的表面,就可以知道從中漁利的是哪些行業——軍火製造商、石油和採礦公司、私人保安公司的傭軍,災後重建時乘虛而入的銀行和開發商,至於Sterling所擔心的,跨國公司與全球窮人之間會爆發戰爭的想法似乎一點也不現實。
《網路島》裡面的世界裡面到處都是看起來跟記錄表現數據的Apple Watche和Nike跑鞋非常相似的消費類設備。但是就像Brendan Byrne在《Arc》中所指出那樣,對消費電子產品和企業網路的每一次準確了解,它的結局都讓人感覺不太好。在洩漏、駭客以及吹哨者(Whistleblower)的揭露下,一場國際陰謀被放到Net上,被所有人都看到了。其結果是對權力的一次沖擊,一場小規模的革命。在這場革命中,公眾對揭露的這些東西的憤怒帶來了真正的政治變革,大批的錯誤得到糾正。再看看我們這個現實的2020年代,感覺每天都有不公被揭露出來,但我們對公正的希望已經迷失在無限滾動的信噪比當中,這種情況下小說的想法顯得有點天真。
《軟體》(Sofrware)
魯迪·拉克(Rudy Rucker)

1980年代的電馭叛客小說不是每本都像Sterling那樣鎖定的是2020年代,但其中的許多人也用別的方式抓住了時代精神。Rudy Rucker的經典科幻小說《軟體》(Software,1983)就是這樣,這是一個把後奇點的未來設定在2020年的故事。乍一看,如果用現實的2020年的角度審視的話,Rudy的世界是完全是認不出來的:機器人,也就是所謂的bopper,已具備自我意識,開始飛往月球上的城市,而被落下的人類則試圖上傳自己的意識與之競爭。但是隱藏在這種高科技情節背後的,是我們非常熟悉的,埋藏在我們心中的憂慮:隨著老去的嬰兒潮一代想要在這個瞬息萬變的世界中努力尋找自己的位置和身份,大家產生了明顯的世代焦慮,而人類爭相想要被上傳,跟我們目前為負擔得起的醫療服務而戰的感覺非常相像。
很容易看出這些希望和恐懼的根源是什麼——1980年代也是技術變革似乎十分迅猛且沒有盡頭的時代。那十年剛開始的時候很多人還沒有真正了解電腦是什麼,但到了十年末的時候已經在日常生活的許多方面都使用起電腦來了。從冰箱到微波爐,每一種家用電器突然之間都裝上了晶片,視訊遊戲和VCR重新定義了娛樂以及我們與之互動和消費的方式。這是一段激動人心的時光,但同時也引起了著新的焦慮,比方說,大家都感到擔心,害怕每次新技術浪潮自己要是跟不上的話就會被淘汰,被遺忘,變成多餘的人。《軟體》及其續集(《濕體》、《自由體》)完美地捕捉到了這種恐懼,而且當然,這種恐懼在今天仍然能引起共鳴,令Rucker那鐵克諾嬉皮(techno-hippie)的角色以及古怪迷幻的小說的作用再次得到體現。
👉 歡迎加入T客邦telegram ( https://t.me/TechbangNEWS )
《過關斬將》(The Running Man)
史蒂芬·金(Stephen King)

大家對技術的加速發展會如何影響到文化和經濟的擔憂是1980和90年代的關注焦點,以至於通常跟這種題材不相關的作家都對2020年代設定的那個不久的將來持懷疑態度。1982年,史蒂芬·金用以理查德·巴赫曼(Richard Bachman)筆名寫作出版了《The Running Man》,故事設定的背景是2025年一個敵托邦的美國,貧富極其懸殊,治安靠高壓維繫,每天市民都要為了金錢參加一個暴力的角鬥電視節目。由阿諾·史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主演的同名電影改編版於1987年上映,電影基本上還原了小說,除了部分細節以外——在電影裡面,參賽者被描繪成罪犯和持不同政見者,而在書中,主角Richards則是出於絕望,為了讓自己掙扎中的家庭擺脫極度貧困而自願參加節目。在小說中,遊戲的跨度需要幾個星期,而不是電影的一個晚上,而且競技場遍布整個美國,這使得史蒂芬·金可以對整個美國社會做出預測,並且關注更加普遍的種族與經濟崩潰這樣的問題。
《人類之子》(The Children of Men)
菲麗絲·桃樂絲·詹姆斯(PD James)

另一位一般不會跟科幻或未來扯上關係的作家是犯罪小說家PD James,1992年他發表了《人類之子》,這是另一本改編的電影比原著出名的小說。這本書和電影都著聚焦在生育力的突然崩潰上面——故事背景設定在2021年, 男性的精子數量莫名其妙就下降了,低到人類根本無法再繁殖的地步。於是經濟再度崩潰,不平等加劇,法西斯主義冒頭。
儘管2006年上映的那部改編的電影傑作以逼真到可怕的手法刻畫了一個衰敗的國家而著稱,但原著卻有一些令人著迷的想法是電影所沒有的——比方說,作為對孩子的替代,大家越來越痴迷寵物,甚至用到了各種極端的方式來表達這種寵溺,包括給它們穿衣服,推著嬰兒車,甚至舉行洗禮儀式。需要指出的是,對於2020年代使用社交媒體的任何人來說,這已經沒什麼可大驚小怪的了。不孕未必是其背後的驅動因素,現如今,大家往往會有這麼一種感受,那就是人們把部分潛在的父愛給予自己的寵物而不是孩子了。的確,對未來的經濟壓力和焦慮正在令許多千禧一代失去要孩子的勇氣。
《過去式》
《星際迷航:深空九號》劇集

1995年播出的《星際迷航:深空九號》的其中兩集《過去式》同樣值得一提,因為它看起來太不典型了,有著可怕的預見性。甚至連《星際迷航》,這部往往以刻畫遙遠未來、技術烏托邦以及星際跳躍著稱的太空劇,也無法擺脫1980、90年代對崩潰的那種普遍的恐懼。第一集開始的時候,因為瞬時傳送裝置出現錯誤,把三名太空人送回到了2024年的舊金山。其中兩位因無家可歸而很快被逮捕,然後扔進了給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準備的「庇護區」(其實是在城市內設置的封閉拘留所)。
相比之下,第三名太空人就比較走運,他被一位真正的技術億萬富翁發現了。後者靠在網路(不好意思,搞錯了,是「interface」)上經營媒體平台以及拿到政府數據挖掘合約而發財。故事隨後發生了更為激進和政治的轉折——劇中的角色意識到,必須要確保庇護區發生一場騷亂,才能引發星際聯邦(the Federation)誕生的政治事件,否則的話聯邦將不會存在。如此看來,《星際迷航》和平、科學驅動、後稀缺性的烏托邦似乎不僅建立在加州的技術上,而且還建立在抗議和革命之上。
用今日的眼光來看,Butler《寓言》系列裡面的很多內容說不定就是從今天下午的Twitter上照搬過來的。
《播種者的寓言》與《天才的寓言》
奧克塔維婭.E.巴特勒(Octavia Butler)

有兩部背景設定在2020年代科幻小說以準得可怕的預見性超越了同時代的所有其他作品:那就是Octavia Butler的《播種者的寓言》(Parable of the Sower ,1993年)以及《天才的寓言》(Parable of the Talents ,1998年)。這位已故大師的這兩本書瞄準了2024年的洛杉磯,並以被氣候變化所帶來的洪水、風暴和乾旱肆虐的加州為背景。中產和工薪階層在門禁社區擠作一團,試圖靠成癮性藥物和VR頭盔逃避外部世界。新宗教和追逐陰謀論的邪教開始興風作浪。為了逃避生態和社會崩潰,一大批難民開始北上,而一位受到福音派基督徒支持的極右翼極端主義總統打著我們熟悉且不寒而慄的旗號——「讓美國再次偉大」當政。
儘管用今日的眼光來看,Butler《寓言》系列裡面的很多內容說不定就是從今天下午的Twitter或今晚的晚間新聞照搬過來的,但也有些內容比較牽強。第二部以主角創建的新宗教的信徒們,乘坐太空船離開地球去殖民半人馬座阿爾法星而告終。Butler原本計劃用第三部來描寫星際探險家的命運,但不幸的是,2005年她去世了。現實的2020年代似乎已經把這種日常的敵托邦呈現在我們面前,對於努力接受的這種敵托邦的我們來說,她留給了我們的兩部曲依舊更接地氣,熟悉得可怕。
這種準得可怕的精度倒從來都不是她的目標。
1998年Butler 在MIT的一次演講中曾談到過這些書:「這不是一本關於預言的書,而是一個假設的故事。這是一個警世寓言,儘管有人告訴我這是預言,但我要說的是,我當然不希望這樣。」
在那次演講裡,Butler詳述了驅使她寫下這一警告的恐懼:對氣候變化的爭論,勞工權利的受損,私營監獄業的興起,以及媒體越來越拒絕談論所有這些,而熱衷於政治宣傳、名人八卦。這都是些我們今天非常熟悉的恐懼。
結語
在評價有關未來的新老科幻小說時,要考慮的最重要的一點也許是——不要在細節、預測準不準或者有沒有過時上面糾纏。把未來準確預測不僅是科幻小說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也是其最無趣的目標之一。科幻小說從來都無關未來,而關乎的是現在。寫未來顯然會折射講述的那個時期的願望、關切和恐懼。
這就是1980、90年代的科幻小說有那麼多的主題似乎在2020年代重複上演的原因:當你的福祉似乎跟經濟興衰的脆弱週期聯繫在一起時,對經濟崩潰和不平等的恐懼也就不難理解。當每週店裡都有那麼多更新更小更強大的電子產品讓你不知所措時,擔心科技可能會讓你失去政治控製或甚至你的人性也就不足為奇了。這也是氣候變化首次能製造新聞的時代,儘管這一議題還沒有找到足夠迅速引起公眾意識的門道,但顯然已經引起了科幻作家的興趣。回顧這些作品時,看它們講對多少件事是很有趣的。一些細節可能會弄錯,可能給消費者產品取了一些似乎很傻的名字,或者沒能預見到智能手機的到來,但卻與我們這個時代所擔心的問題卻相當接近,是作者能夠把握我們周遭世界的趨勢、變化以及沖突的能力之證明。
所以,也許是時候得重新評估一下什麼叫「過時」了——不妨少一些批評,多一點掌聲。這意味著小說或電影是「有時間印記」的,說不定可以充當重要的歷史文獻,或者作者(以及更廣泛的社會的)夢想與夢魘的時間膠囊,說不定還可以給我們一些關於未來,那個有待我們去塑造的未來的經驗教訓。
👉 歡迎加入T客邦telegram ( https://t.me/TechbangNEWS )
- 資料來源:How Science Fiction Imagined the 2020s
- 本文授權轉載自36Kr

請注意!留言要自負法律責任,相關案例層出不窮,請慎重發文!